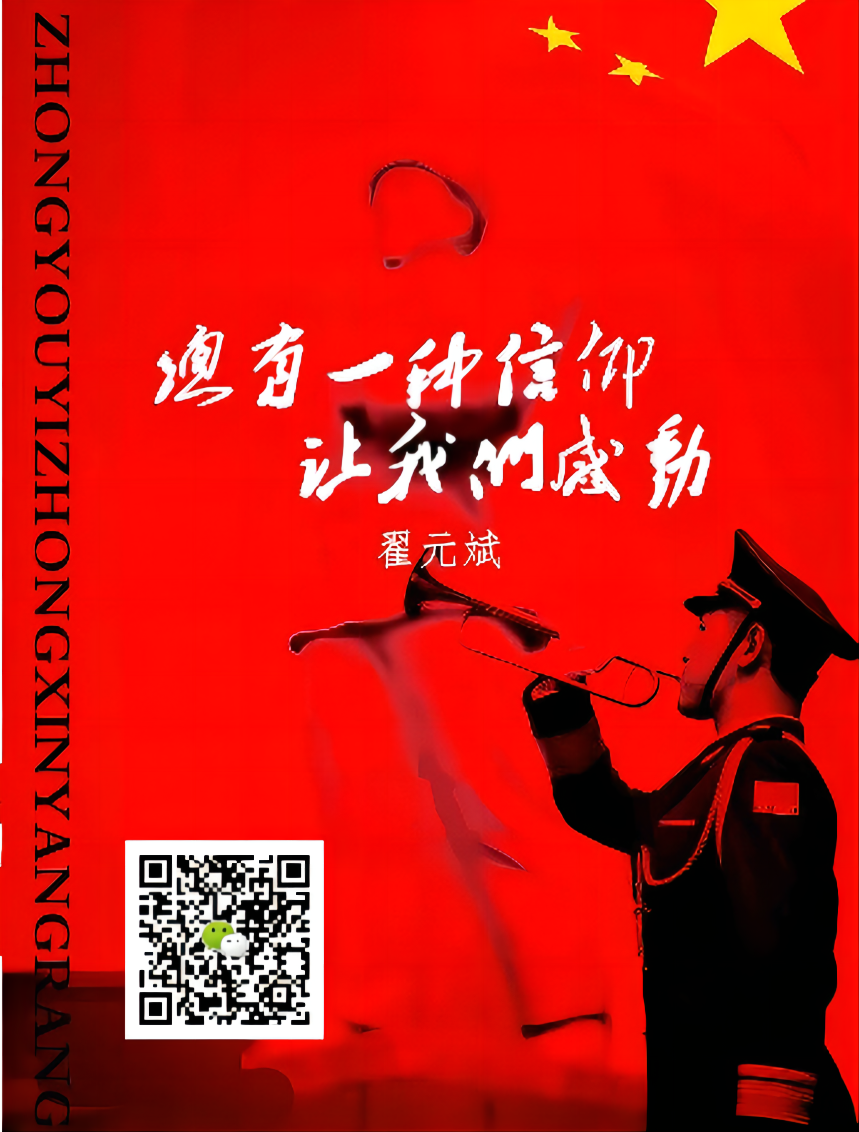|
翟元斌‖像雷锋那样热爱生活 【访谈录】翟元斌‖像雷锋那样热爱生活 【访谈录】 ——雷锋精神研究所所长翟元斌访谈录
从1963年起,3月5日就因为一个人而变得不再那么普通,他在几代人的心中是助人为乐的典范,在孩子们的课本中是位永远带着笑容的叔叔,在年轻人的口中是舍己为人的代名词,他就是雷锋。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,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怀念离开我们近50年的他。 正如雷锋精神研究所所长、《雷锋精神研究》杂志主编翟元斌所说,在很多人担心雷锋即将仅仅成为一个代号,甚至即将消失的今天,《雷锋日记选》、《雷锋的故事》、《雷锋》、《伤痛无声——乔安山忆雷锋》、《雷锋第二故乡的坚守与超越》等书的接连出版,这就表明,雷锋不曾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,雷锋在每个时代、每代人的眼中都有不同的价值。
雷锋的信仰叫忠诚
《雷锋日记选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,我要把有限的生命,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……”这句话,即使在今天那我们读起来,也能让人心中暗潮汹涌,这就是雷锋精神,他教会人们的是对党和人民忠诚,他教会人们的是对党和国家、对事业要忠诚。 很多人都将雷锋精神归结为无私奉献、爱憎分明等,翟元斌告诉记者,通过他对雷锋的多年研究发现,其实雷锋精神,也可以说是雷锋的信仰叫做忠诚,这就像是一种精神状态,当一个人对祖国忠诚、对事业忠诚、对生活忠诚,他就也会成为像雷锋一样的人。雷锋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,甚至他受教育的条件与今天相比都很为苛刻,可就是那样的一种环境丝毫没有影响雷锋心灵的纯净,当翻开《雷锋日记选》时,那种扑面而来的激情和忠诚之感,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
每个时代都需要感动
曾有人对雷锋在当下时代的价值产生了怀疑,甚至会有人提出,雷锋的存在只是一个形象而已,雷锋的精神早已过时。但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,一些家长出于怀念,买回家一些与雷锋有关的书籍给孩子看,却发现孩子读的是那样的出神,感兴趣的程度完全超出了父母的想象。翟元斌表示,其实这并不难理解,《雷锋》、《雷锋的故事》等书籍让孩子感到亲切,是因为人都是需要感动、渴望帮助的。 当孩子们在教科书和课外书中读到雷锋时,他们的心灵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,他们知道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是可以这样的和谐,彼此之间可以这样的信任,对待社会和生活应该忠诚,被吸引自然就成为了理所当然,甚至可以说,这是一种心的呼唤。 在物质进步的同时,时代也需要精神的进步,青年人心灵疲惫时、老年人需要慰藉时,不妨都翻开与雷锋有关的书籍,让那份感动来填补心灵上的空缺。
像雷锋那样热爱生活
雷锋是英雄,但也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也是一个会被衣食住行、七情六欲所困的人,同样,雷锋也是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,我们今天有人爱唱歌跳舞、会遇到情感问题、爱穿漂亮衣服等等琐事,雷锋也都会遇到,甚至可以说,雷锋可能比现在的我们更会为人处事,更懂生活。 雷锋两个“人尽皆知”的爱好,一个是唱歌跳舞,一个是照相,雷锋除去英雄的称号外,也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小伙子,他热爱生活给予的每一次欢乐,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自己留影,从这点看,他与我们今天的80后、 90后又有什么区别呢?都是那样的热爱着生活。 在关于雷锋的纪实体小说《雷锋》中讲到,为了参加工厂组织的舞会,雷锋也会有爱美的想法,买了皮夹克、手表和当时流行的料子裤,可这样的行动却被老领导提出了“不要忘本”的教育,深知全国人民还未富起来的雷锋,于是将自己的这套行头收了起来,并把自己剩下来的钱捐给了需要帮助的人。雷锋就是这样一个人,热爱生活,懂得生活,也更加懂得约束自己,在自我的管理中寻求生活的乐趣。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“雷锋”
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“雷锋”是爱党爱社会的典范,九十年代的“雷锋”是生活中的楷模,而今天的“雷锋”,除去过去人们看到的雷锋精神外,还可以看到他在成功学、心理学等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影响。 翟元斌告诉我们,工作中样样优秀的雷锋,在最初申请入伍时是不符合要求的,曾被拒之门外,但雷锋硬是凭他坚忍不拔的毅力、水滴石穿的耐力、令人钦佩的情商,为自己赢得了破格录取的资格。这对于今天在职场上苦苦挣扎的白领来说无非是最生动的教科书,成功学的魔力在雷锋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。 除此以外,雷锋也曾受过传言的困扰,曾经有人说过他与谁家的姑娘情投意合,但雷锋靠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实际行动很快平息了传言,并保持了与女性朋友间正常的友谊。所以说,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雷锋,雷锋的精神也会在每个时代呈现自己的独特之处。 除了雷锋精神内容在时代作用下的充实,雷锋精神的宣传也启用了不少的新形势,如互联网上开设的雷锋博客、雷锋吧,成立雷锋论坛,设计雷锋的动漫、卡通书、文化衫等,多样化的宣传手段都将为雷锋精神的传播搭建新的平台。 同时,雷锋的第二故乡抚顺市也将在今年的三月推出《雷锋第二故乡的坚守与超越》,从新的角度解密雷锋史料、解读雷锋事迹。
注:翟元斌 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所长、《雷锋精神研究》杂志主编 原载《辽沈晚报》读书
|